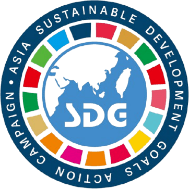COP30@ASIA SDG Action Education & Campaign
COP30@ASIA SDG Action Education & Campaign
全球氣候政治的轉折
自《巴黎協定》於2015年生效以來,全球氣候治理已歷經從「目標設定」到「行動落實」的轉型。
然而,隨著2025年全球進入「第二輪NDC(國家自主貢獻)」更新期,氣候政治正出現三項根本變化:
1. 多邊秩序的碎片化(Fragmented Multilateralism)
美國再度退出《巴黎協定》,削弱了過去由美歐主導的規範性共識,使「多極氣候治理」逐漸成形。
此舉也促使歐盟、巴西、中國與非洲聯盟等新興體系,積極尋求制度與道德雙重領導地位。
2. 由「承諾政治」轉向「執行政治」
各國的焦點從宣示減碳目標,轉向實際執行、資金落實與技術可行性。國際社會更關注誰能落地、誰能資助、誰能監督三大問題。
3. 氣候治理與地緣政治的融合
能源、糧食、科技與安全政策全面交錯,氣候政策不再只是環境議題,而是國家競爭力的延伸。
中國:從執行者轉為制度設計者
• 以「綠能規模+南南合作」成為實際落地的行動中心。
• 2024年後,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資國,並藉由「南南氣候合作白皮書」建立國際技術援助體系。
• 中國的氣候外交路線呈現三大特徵:
—經濟導向(投資與供應鏈);
—科技導向(電動化、儲能、氫能);
—制度導向(合作機制、基金平台)。
中國的氣候領導力正在轉化為一種「可供輸出的體制模型」,成為南方國家追隨的實踐範例。
巴西:以森林與正義打造南方道德領導
巴西藉COP30主辦國地位,推動「亞馬遜氣候倡議」,強化熱帶雨林治理與原住民議題。總統盧拉主張建立全球熱帶雨林基金(Tropical Forest Permanent Fund),以「自然資本正義」挑戰北方國家長期壟斷的金融規則。此外,巴西積極整合拉美與非洲國家,在G77框架內強調「森林=全球公共財」的新倫理。
歐盟:規範輸出與碳邊境新秩序
歐盟透過CBAM(碳邊境調整機制)與ESRS(歐洲永續報告準則)推動「氣候合規的經濟外交」。這種模式雖維持規範優勢,但也被南方國家批評為「氣候保護主義」。其挑戰在於如何平衡內部減排壓力與外部公平性。
印度與非洲聯盟崛起
印度以「低成本能源+碳捕捉技術」尋求能源安全與發展平衡。非洲聯盟(AU)則以「損失與損害基金」為平台,要求補償性融資與技術移轉。兩者正聯手構築「氣候正義陣線」,意圖在COP框架內形成制度化的南方協調機制。
G77、中國、巴西、印度與非洲聯盟正逐步形成氣候南方聯盟(South-South Alliance)。
這一新體系將挑戰過去「北方出資、南方執行」的單向結構,推動資金共管與知識共創的新秩序。
而在美國退席後,中國與巴西的雙重領導模型——前者代表「執行與技術」、後者象徵「倫理與生態」——正在塑造一種新的南方氣候秩序。
未來的氣候政治,將不再是權力的競賽,而是價值的競爭。
真正的領導者,不是碳排最少者,而是能讓世界「共生」的創造者。
©2025 - Asia SDG Action Education